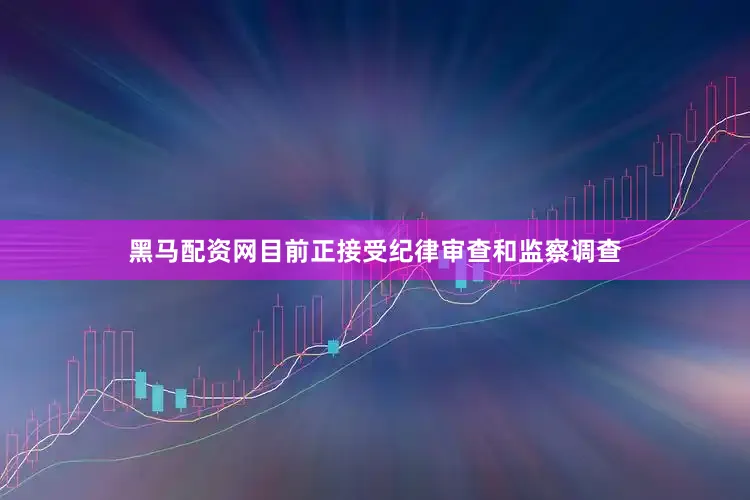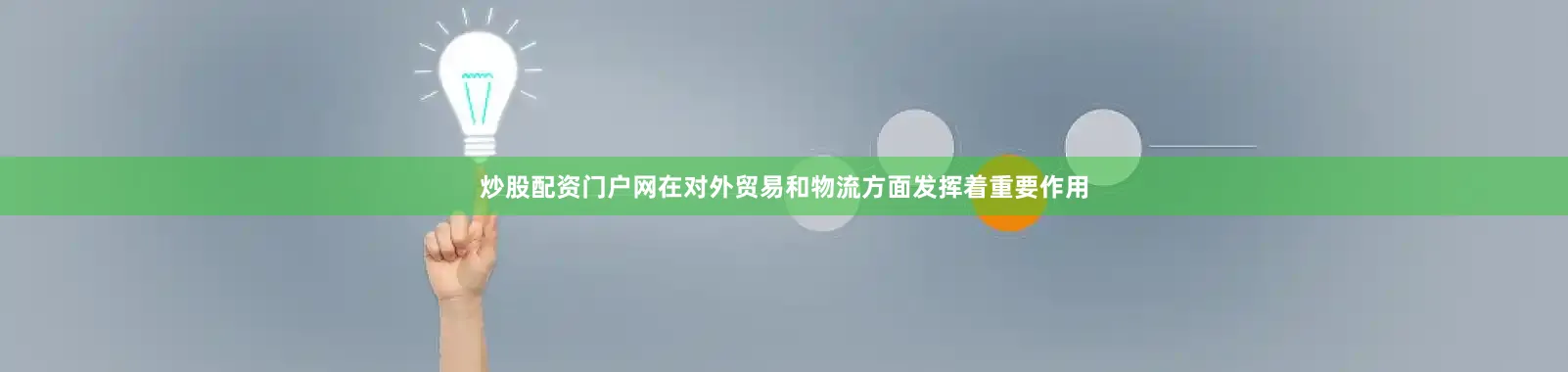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日,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凌迟处死并传首九边。熊廷弼之所以获此重罚,除了兵败、弃土、党争等因素之外,他自己的“嘴”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。
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惨败,辽东乃至明廷大为震动。就在人心浮动之际,刚被朝廷委以重任(辽东经略)的熊廷弼,又扔出个“大炸弹”。在他口中,辽人不说全员当了汉奸,也个个都是潜在的投敌分子。
今沈阳皆已逃尽,辽阳先逃者已去不复返,见在者虽畏不敢逃,而事急之时臣安能保?况辽人浸染胡俗,气习相类。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,不恨,而公家一有差役,则怨不绝口。贼遣为奸细,输心用命,而公家派使守城,虽臣以哭泣感之,而亦不动。 《辽左大势久去疏》熊廷弼这么夸大其词主要有两个原因。
其一,辽东的颓烂让他一度信心全无,有了放弃的念头。他甚至建议神宗放弃河东,退守广宁乃至山海关。其二,熊廷弼不同意朝廷推行的“辽人守辽土”,他觉得依靠辽人守不住辽东。
展开剩余85%熊廷弼观点的对错,大家可以各抒己见,但他这种口无遮拦的表达方式绝对有问题。
首先,这么丧气的奏疏让朝堂对他有了很不好的印象,遇事就想撂挑子。天启处死熊廷弼的诏书,开头就提到了这点。其次,这么无差别地责辱辽人,是非常得罪人的。和熊廷弼本无仇怨的兵部主事刘国缙(辽东复州人)会盯着他,不能不说有这份奏疏刺激的原因。
骂完“辽人”熊廷弼并未收敛,又转头开始骂朝堂同僚、特别是他的上司们。
由于熊廷弼坚决不同意“辽人守辽土”,兵部只能尽量从关内各镇抽调兵员输送至辽东。这不仅是增加了军队调拨的开销,由于必须定期让军士轮休返家(不然就形同流放了),这也加大了兵员调拨的频率和数量,进一步增加了军费。
按照熊廷弼用兵18万、马九万匹的规划,士兵每年需饷324万两、粮108万石(马匹年需豆97.2万石、草2160万束)。这18万士兵如果全部从关内征调,粮饷起码还要翻五成。
以当时明廷的穷困,加征了辽饷也支付不起,调兵的实际进度自然也满足不了熊廷弼的要求。
但熊廷弼并不在乎朝廷的实际困难,调兵慢了他上奏疏责难兵部主事官员、粮饷发运不够他弹劾户部的相关官员。关内调派至辽东的士兵因畏惧苦寒或忧心无法归家而逃亡,他一样要责骂兵部 ……
如果靠“骂”能增加明廷的岁入并提高兵部效率,都不用熊廷弼出面,神宗自己在三大征时就开骂了。但熊廷弼只是觉得骂的还不够重,因此上了嘲讽味十足的《部调纸上有兵疏》。
兵部尚书黄嘉善、户部尚书李汝华,身担兵饷重担,皆图全躯保妻子,莫有肯为皇上拼死力争上紧干办者,何况各省镇督抚诸臣 ……不但把兵、户两部的尚书和九边封疆大吏们骂了个遍,他连神宗也没有放过,直接质问“皇上深居静摄,禁不闻声,请问皇上要辽东否”。这样除了得罪人、无端拉仇恨,还有啥作用?
好在万历的脾气涵养还行,要是换成洪武、永乐、嘉靖、崇祯中的一个,就算不死也妥妥的下岗问罪,但熊廷弼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。
熊廷弼能在辽阳笑骂朝堂上下,不是大家都怕跟他斗嘴皮子,而是神宗将绝大部分弹劾他的奏疏“留中不发”给拦了下来。神宗驾崩后,朝廷很快就因弹劾而启动了调查熊廷弼的程序。
“移宫案”功臣杨涟则利用熊廷弼坚决不服软的性格,两句话就把他激得自请辞职了,“刚烈男子一刀两断,端不宜效近来顽钝行径,既不认作,又不肯去,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国家”。
除了把熊廷弼搞下岗,杨涟还两句话就否认了熊廷弼一年经略之功,“议经略者终难抹杀其功,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咎。功在支撑辛苦,得一载之幸安,咎在积衰难振,怅万全之无策”。
这不仅让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半途而废,也证明熊廷弼的嘴皮子功夫、朝堂斗争能力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强。
天启元年三月,辽沈失陷,天启和明廷有意重新启用熊廷弼。但熊廷弼并未总结初任经略的教训,依然放任自己的“嘴”惹事。
前文提到熊廷弼首任经略之初,让朝廷对他有了一个很坏的印象 -- “遇事就想撂挑子”。而这次熊廷弼一样从一开始,就在加深天启的这种印象。
面对朝廷的起复召令,熊廷弼一开始是拒绝的。但他拒绝的并不坚决,仅是以抱病推诿(坚决拒绝大多用“无能”、“无法胜任”等理由)。后天启放下身段亲自下敕,自称少年登基难堪大任、恳请熊出山相助后,熊廷弼就改口领命了。天启没把这事儿视为“三顾茅庐”的重演,只觉得熊是在摆谱。
熊廷弼到任后,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,他这个辽东经略成“光杆”了。但这事并不能简单指责辽东巡抚王化贞贪夺经略的权力。
首先,辽东经略虽然是辽东巡抚的上级,但这更多是名义上的。因为依照明廷制度,两者均有“便宜行事”之权并直属兵部监管。也就是说熊廷弼如果想指挥王化贞行事,得通过兵部下达命令。
其次,明朝的巡抚、总督、经略的职权都是有具体辖区的。辽东经略被划定以河东(辽阳、沈阳为核心)为基地,总司征剿女真事务。辽东巡抚则驻守辽西,配合经略平叛并总揽对蒙事务。
辽沈失陷后,辽东经略的地盘没有了,在物理上就成了光杆。所以王化贞会认为熊廷弼是空降下来摘桃子的人,天然就会排斥他。熊廷弼宦海浮沉也几十年了,其中关窍他应该很清楚,但他在和王化贞的沟通中并未表现出他明白或者在乎这些。
熊廷弼认为自己这个经略当掌控战略谋划和部署,王化贞这个巡抚则应去具体执行和实现自己制定的方略。王化贞自然难以接受了,再加上两人一个主攻(王)、一个主守(熊),谈都谈不到一起去,更别说配合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熊廷弼又写了一封书信“规劝”王化贞。
首先,提及两人当年在辽东的共事之情。并质问王化贞为啥之前没矛盾,自己一出任经略,你就不听规劝了呢?
其次,历数王化贞出任巡抚后的失职。诸如没安排好后勤、前线官兵逃军、战马准备不足等等。熊似乎忘记自己初任经略时,在这些事务上是怎么责骂兵、户二部的。
第三,熊廷弼又从军事角度将王化贞当前的部署详细点评了一番。简单来说,就是一无是处(包括安排毛文龙偷袭后方)。最后,熊廷弼直言王化贞看信后会暴怒,希望他能平复心情、好好体谅他的用心。
如熊廷弼所料,王化贞见信后气得暴跳如雷。此信也成为两人关系破裂的标志,王化贞此后行事不但不与熊廷弼沟通商议,甚至刻意去抵制和反对熊廷弼的所有提议。在说王化贞能力、情商不高的时候,真不能高估熊廷弼的能力和情商。
广宁惨败后,熊廷弼决然下令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(王化贞自行留在宁远前屯卫)。然后在山海关连上《封疆已失疏》《辽事是非不明疏》《请发从前疏揭质对疏》,试图说明关外惨败不是自己的责任。
姑且不论明廷针对他们经抚不和,定下的“同功同罪”。作为封疆大吏,朝廷没有下令弃土,死也应该死在关外。
而且熊廷弼这一番自辩,在天启眼里是坐实了他“遇事就撂挑子”。不然天启不会在熊的绝命诏书里说,“乃熊廷弼欺朕即位之初,始则托病卸担,荐袁应泰而辽阳亡,既则刚愎不仁,望风先逃而河西亡”。
编者附:
熊廷弼被判死罪后,一直觉得自己罪不当死被冤枉了,专门写了《辩冤疏》希望能上呈御前。即便不能免罪,起码也能向皇帝辩解冤屈,寻求一个心理解脱,只是一直无人愿意替他转呈。行刑当天,监刑官张时雍正好问到了他随身带着的《辩冤疏》。
这本是熊廷弼最后的机会,但他受不了张时雍带有讥讽的调侃。嘴上不饶人的习惯,让他毫不犹豫地把张反怼了一番。张怎么会帮他转呈?
熊既奉旨,从容更衣以出,胸中盛一小袋,内具辩冤疏,提牢主事张时雍问曰:“袋中何物?”熊曰:“辩冤疏也。”张曰:“公未读李斯传乎,囚安得上书?”熊曰:“君亦未读李斯传,此赵高语也!”以疏稿授张。受刑后,传首九边,尸弃漏泽园,疏卒不果上。
《三朝野纪》
发布于:上海市启盈优配-杠杆配资平台-股票配资机构-散户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广州股票配资平台交流比如干煸豆角;吃海鲜的话
- 下一篇:没有了